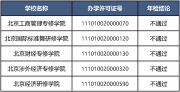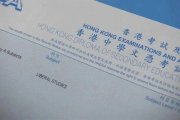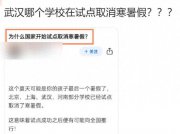摘要: 原标题:比较中美两国高等教育体制之时 但人文教育本身的退化也不可忽视 在比较中美两国高等教育体制之时,一个常被提及的差异在于,后者人文学科
原标题:比较中美两国高等教育体制之时 但人文教育本身的退化也不可忽视
在比较中美两国高等教育体制之时,一个常被提及的差异在于,后者人文学科体系更为健全,并且被完善地编织在本科教育课程当中。这样一种教育模式通常被称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或者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

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在入学的前两年先不急着确定自己的主修专业,而是在各类课程中尽可能多地尝试不同学科,以寻找自己的兴趣的过程中,拓展知识面。另一方面,它的人文学科课程也更多基于经典著作、以及西方的文化传统,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以及公民意识等。
然而,作为通识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史哲等学科正在面临危机。以历史为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历史学者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和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 Gavin)认为,这门学科正在慢性自杀。“近几十年来,专业的历史学者已经距离学生和大众越来越遥远,并且逐渐不再与当下的政治、外交、战争、和平等关键事物产生关联。”“历史学科正在逃避自己的责任,不再与外界世界接触,并且探讨当今美国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他们认为,这种倾向使得学生远离历史。自 2008 年以来,选择历史作为主修课程的学生数量下降了超过 30% 。而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字,自 2007 年到 2016 年,获得文史哲这传统人文通识教育的三大类专业本科学位的人数,分别下降了 22%、25%、以及 15%,而同一时段,选择商科、工程、以及计算机科学的人数分别上升了 24%、705%、以及 85% 。
与此同时,校方也削减了通识教育的投入。2019 年 1 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所分校宣布将砍掉一些与通识教育相关的学科,如历史、德语、法语,以应对不断上涨的财政赤字,以及日益减少的学生数量。校方表示,大学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多可以帮助他们未来职业发展的教育机会,以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
经济学者大卫·布伦尼曼(David Breneman)的研究则认为,专门从事通识教育的文理学院将会从 1990 年左右的 200 所逐渐下降至 120 所。从学科,到学生,再到学校,通识教育都在经历一段艰难时光。
“没有历史专业的大学还算是大学吗?”《纽约时报》关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所分校的报道援引了一位学生对校方的质问。这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将通识教育衰落视为危机的人的观点。《纽约时报》的另一篇社论,在批评大学的上述做法后指出,当今的高等教育变得过于就业导向,也就使得通识教育在大学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微信图片_20190319182115.jpg
▲ 《死亡诗社》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社会,将教育视为一种帮助找到好工作的工具,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人们都相信,教育能够改变人们的命运,成为社会不同阶层向上流通的渠道。
尽管许多学者的研究都指出,将提升社会阶级的希望放在文凭之上只不过是一种神话。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ins)就出版了《文凭社会》一书,并指出教育并没有促进社会平等,社会阶级并没有因为教育而改变多少。而父母的阶级才是影响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主要因素。
然而,神话本身的存在却始终在影响学生的选择,尤其是对于专业的选择之上。由于技术人员的重要性逐渐提升,选择就读相关专业的学生更容易在毕业后找到高薪的工作,而在过去几十年中,金融业和程序员就是其中的代表。
人类学者何柔宛曾经在华尔街工作。“24 岁就拿到每年 10 万美元的薪水在 1990 年代的华尔街前台部门是正常的标准。对于 MBA,一般是华尔街的经历,在他们还不到 30 岁,入职的第二年开始就可以收入 20 万到 30 万美元。”在其出版的《清算》一书中,她这样描写华尔街,“这种薪酬制造出了一夜致富的宣传效果,以至于大多数华尔街人总是固守着这份他们常常并不享受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同样的词句似乎也可以形容程序员的生活。尽管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强度较大,但学生们仍然在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或者报读一些计算机相关课程,以便日后能够进入互联网公司。而吸引他们的很大因素便是互联网行业年薪百万的神话。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学费也正在不断上升。2017 年美国私立大学平均学费 35720 美元、公立学校为 10270 美元。过去十年中,大学教育的费用和其他与学校有关的费用增加了 63 %。
学费的上涨幅度远超同期的通货膨胀水平,也就迫使学生通过助学贷款的形式完成自己的大学教育。相关数据显示,美国近四分之一的成年人需要承担助学贷款,贷款总规模已经超过 1.5 万亿美元,平均每人的债务达到 29650 美元。在债务的压力之下,如今入学的学生自然更倾向于选择容易就业的学科,而非人文学科。
这样的选择倾向,在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平民化的背景下,则会被进一步强化。根据美国教育部的数据,美国高中毕业生选择进入大学就读的比例从 1960 年的 45.1% 上升到 1998 年的 65.6% 。而由于美国人口总量不断增长,绝对入学人数的增幅要更明显,从 2000 年到 2016 年,就读于 4 年制学位和 2 年制学位的总人数从 1320 万人增加到 1690 万人,并预计将在 2027 年达到 1740 万人。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学教育依然主要面向富家子弟、名门之后。然而,在随后繁荣的 20 年里,出现了大学数量和入学人数的大幅增长(现在,全国有 1400 多所四年制的学院和大学),以及对大学学位益处的渴望的普遍蔓延。”在《椰壳碗外的人生中》,以研究民族主义成名的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这样写道。
随着高等教育成为唾手可得之物,高等教育之于学生的意义也在逐渐改变。如果说以前人们还将高等教育视为获取知识的途径的话,那么现在人们也更容易将它看作是一种投资,通过文凭在未来获得更高的薪资。由此的结果便是,金融、工程、法律、医学这些专业性课程的诱惑在增强。而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就会逐渐缩减。